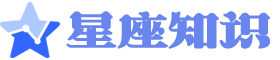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 出道仙和出马的区别
你现在浏览的是一篇关于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的精彩内容,本文拥有出道仙和出马的区别和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的精彩内容发布,喜欢的关注本站。
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 出道仙和出马的区别
出道与出马杂谈 出马、出道的仙家,到底谁的道行高?
一、出马、出道的仙家,到底谁的道行高?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例子来比喻,出道的仙家好比大学毕业,出马的仙家就是还没有毕业,在校和离校的都有学习很好的,所以问在校和离校的学生,谁学习好这个问题,实在不好回答。
理论上个人认为,出道的仙家所谓的学历,要高于出马的仙家,也就是说,出道的仙家都应该,经历过出马的过程,出马的仙家经历了,几次出马的经历之后,会最终走上出道的道路,但是并不代表出道的仙家,道行一定要高于出马的,很多出马的仙家的“学习成绩”,是很优秀的,也许就是差在功德不足,或者心性不足等原因,还达不到出道的资历。
二、再谈出马、出道看事的区别
很多弟子,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尤其是出道的弟子,始终对于出马弟子,出堂就能看事始终耿耿于怀,尽管很多资料都表明,出道仙家的“学历”高于出马仙家,但是就看事能力来看,出道的弟子,确实不如出马的弟子。
看事能力主要在于仙家捆身上,出道的仙家不喜欢捆身,出马的仙家都是捆身看事,出马和出道的区别,还存在于另外一个方面的因素,占窍!
不管出道还是出马的弟子,对占窍、串窍(打窍)没有不知道的,其实占窍和串窍(打窍)不是一个概念,从流程上讲,出马和出道的弟子,从串窍开始之前的整个经历,大致是这样的。
①是教主或者碑王选择弟子,要从资质、心性、香火传承等方面来考察的。
②如果是教主选定弟子,则教主指定碑王,全面负责串窍进度,由碑王、清风先期串窍,随着进度的开展,碑王会安排胡、黄、常、蟒等,各家仙家按照次序串窍,如果是碑王传承香火,会由碑王安排串窍,并由碑王负责召请教主、仙家陆续来堂口落座。
③教主负责召集堂上人马,决定可以上身串窍的仙家,出马和出道的区别差异,在这里可以体现出一点来,出道的仙家不是每个仙家,都可以捆弟子身体看事看病的,所以说单独有占窍的定义,出道弟子经历了养堂期之后,可以很清楚的说明,每个仙家上身时候的具体位置,大概可以精确到,一个拳头大小的范围,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出道的弟子会有,每个仙家单独占弟子身上一个窍,而不像出马弟子那样,每个仙家或者每教仙家上身,所占的位置都是大致相同的。
④经过串窍、占窍期之后,出马弟子会点兵看事,出道弟子会点兵养堂。
⑤还有一点是,出马弟子和出道弟子不同的地方,出道弟子会持续出现串窍的迹象,而出马弟子在正式点兵之后,基本上很少出现再次串窍的迹象,这一点和上面的第三点的概念相吻合,出道弟子会随着堂口仙家的增多,而逐渐增加看事的功能,所以会出现新来的仙家占新窍,重新打窍的迹象。
综上所述,打个比方,出马的弟子有点类似于做路边摊,每个仙家都是大师傅,自己去招揽顾客,所以出马弟子有圈堂的说法,因为路边摊的经营很简单,所以有一个或者几个灶就足够了,这个灶就是代表窍。
那个大师傅招揽来生意,就上灶做菜,因此路边摊会因为大师傅的跳槽而关闭,出道的弟子有点类似于做大酒店,掌堂教主就是经理,他会根据酒店的规模、大师傅的手艺,决定对酒店的安排,会对不同的菜系,安排设立不同的厨房、灶台,有的仙家做保安,有的仙家做服务员,有的仙家做厨师,不是每个仙家都能做厨师的,要量力而行,规划长远。
不会象路边摊那样,把车推到路边就营业,要先选址、装修、试营业之后,才能正式营业,大酒店是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决对不能象路边摊那样,随随便便的就能开,就能收,所以出道弟子点兵后,不能看事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三、出马出道其实没有区别,很多弟子都在研究自己,是出马还是出道的,其实没有必要,一言以蔽之,路边摊也总有能做成大酒店的榜样,出马的弟子堂口,还要比出道的弟子多一个授法使者,他就是负责指导,出马弟子修行的,只要弟子肯修,能够把自己的小农意识、开路边摊的眼光,修炼到开大酒店的规划,那么出马弟子,就会逐步转变为出道弟子,路边摊升级为大酒店,再有,大酒店开黄的例子,也不在少数。
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出马和出道最终、最好的发展是殊途同归,所以建议所有的朋友们,要从表面的差异中,看实质的大同!
出马的弟子看事的时候,会滔滔不绝,可以说的合辙押韵,甚至可以唱二人转、地方戏,出道的弟子也不是没有,只不过是没看到而已,但是作为出道弟子,这种现象非常少见,路边摊的顾客提问,大师傅可以张嘴就回答,顾客听的很清楚,如果大酒店的顾客提问,掌勺的大师傅的回答,就得经过层层转达,到顾客耳朵里面的时候,就会走样、衰减,这个信息的流失,是出道弟子必须经历的过程,等到跑堂的服务员,或者大堂经理熟悉业务之后,回答的就会非常熟练,简单的说,就是出道弟子,和堂口仙家的磨合还不够。
出马或者出道弟子,死后到底会怎么样,能不能转世,准确的说我也不知道,总不能因为回答这个问题,我死一次吧,但是原则说清楚了,路边摊可以做成大酒店,大酒店只有做的生意兴隆或者破败,不存在做成路边摊的结果,好人有好报,只要顶堂做好事,弟子死后自然知道好处。
民间故事:狐狸精的修行之法
民间故事:狐狸精的修行之法
清代名臣纪晓岚有位朋友叫刘师退。这个刘师退是个神人,竟可以和妖怪交朋友。其中一个是住在旧沧州难的狐狸精。
一次刘师退专程去见了这位朋友,和它聊了聊关于狐族的修行之法。
此时的狐狸已经可以化形,长得很接地气,身材短小,貌似五六十岁的老人家,穿着不今不古,满发圆领,像个道士。它也跟人一样拱手作揖。作揖时,狐仙看上去很是谦和和恭谨,也很安详平静。
刘师退说:“我们人类和你们狐族世世代代相处,但是关于你们的传说大有不同,里面似乎有很多隐晦不明的细节。听我们共同的盟友说您生性豁达,并不忌讳自己狐族的身份,所以我特意前来求您帮忙解惑。”
狐狸听罢,淡然一笑:“天生万物,会以不同的名字为它们命名。狐之所以叫狐,就像人之所以叫人一样。喊狐为狐,就像喊人为人一样。这有什么好忌讳的呢?至于我们狐族,好坏不一,就像你们人类,良莠不齐,都是一样的。人都不避讳人丑恶的一面,我们狐狸又怎么会忌讳狐狸的丑恶呢?确实没有必要忌讳。”
刘师退对这只豁达的狐狸表达了钦慕之意后,问:“那么狐之间是否有区别?”
“凡是狐都能修道,狐中最有灵气的叫狴狐,打个比方,就像你们人类读书,儒生读书多,农民读书少一样。”
“狴狐生下来就有灵性吗?”
“这关系到遗传,还没成道的狴狐生下来的是普通狐狸,但是成道后的狴狐生出来的小狐狸,刚生下来就懂变化。”
“既然能成道,那一定能做到容颜常驻了,但是小说中也时常出现一些关于老头狐、老太太狐的记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狐族所说的成道跟你们人类得到成仙还不太一样,我们的成道之的事修成人道,蜕去狐身,华为人。真正变成人之后,我们的吃饭穿衣、生老病死。男欢女爱和人一模一样。可以说,这时候的狐狸已经完全变成了人类。
“至于白日飞升,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好比你们人类求学,千百个读书人中,也只有一两个能考中状元做官。飞升成仙可是比千军万马走独木桥还艰难的一件事情。
“狐狸修炼的方式,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服气炼形,一种是媚人采补。”
“服气炼形的狐狸,好比人从小到大不停地学习、积累,学到一定程度,才能考中状元。那些媚人采补的狐狸,好比你们人类那些靠走捷径和邪门歪道暴富的人。
“两种修炼方法,各有千秋。但是,想游仙岛、飞升天界,就必须扎扎实实地炼形修炼才能做得到。媚人采补的,伤人害人太多的,往往有违天律,会受到上天的惩罚。”
“那么,是谁来掌管你们狐族的禁令赏罚呢?”
“小的赏罚由我们狐族首领来掌管,大的赏罚则有当地鬼神于暗中监察。如果没有禁令,那我们狐族完全可以做到来往无形,出入无迹,任凭心意,为所欲为,那什么事是我们狐狸做不出来的呢?”
“既然媚人采补不是正道,那为什么不把它列入禁令,反而等狐族伤了人后才进行惩罚呢?”
“这就好比你们人类有的会设下机关,用种种巧妙的手段骗人钱财,上当受骗的人是自愿出钱的,这事就连王法也没有办法禁止。至于因夺财而杀人的,那就要依法论罪了。”
“经常听说哪个狐狸为人生了孩子,却从来没听说过有人为狐狸生孩子。这是为什么呢?”
狐狸听到这个问题,嘴角勾起一抹笑:“这种问题不值得讨论,因为和人交欢,狐狸重在采补,既然是媚人采补,这种形式注定了狐狸对人只有索取,没有给予。”
“那狐女和人在一起,就不怕他的狐族配偶嫉妒吗?”
狐狸再次一笑:“先生的话太多放肆。看样子您对这一方面的真的毫不知情。跟你们人类一样,凡是未婚狐女,就像那位对鄫子一见钟情未婚少女季姬一样,是可以自行择偶婚配的。而已经成婚的狐女呢,他们恪守妇道,不敢越过男女大防。”
“至于那种赠芍采兰偶然越礼的情况也是有的,不过,这乃人之常情,你们人类中不也有偷情的人存在吗?在这一点上,人和狐没有什么差别,有人及狐,类比一下就可以了解了。”
刘师退了然地点头,再问:“那成精的狐狸,有的住在人家家里,有的住在旷野,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还没有成道的狐狸,兽性也没有脱尽,它们现在还不合适与人过多地接触,住在深山旷野中最合适不过。”
“已经成道的狐狸,处处都和人一模一样。它们适合和人住在一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比城市更适合它们居住的了。”
“至于那些道行的狐狸,城市、山林,来往逍遥,想住哪里就住哪里。就好比你们人类中的富贵人,因为有钱,所以什么都能买到,即使住在穷乡僻壤,也跟住在大都市没有区别。”
疑惑解得差不多了,刘师退开始和狐狸纵谈天地,但是狐狸对此兴致不高,话里话外的意思都是让刘师退珍惜人身,早学大道。
狐狸语重心长地劝他:“我们狐族辛辛苦苦修炼一两百年才能化为人身,先生你现在就是人,修仙已经比我们轻松了一大半。可惜啊,你却天天无所事事,东游西逛,将精力平白浪费在一些无聊的小事上,最终跟草本一样,没多久就枯朽死掉了,实在可惜!”
临别时,刘师退高兴地道:“今天相逢,南史我天大的幸运和福气。您能不能给我一句临别赠言呢?”
狐狸踌躇良久,似乎很为难,最终才下定决心开口道:“自夏、商、、三代以来,恐怕没有不好名的人,但这些大人都沦为了下乘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心平气和,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之态。宋朝那些崇尚程朱理学的儒者,动不动就一副横眉怒目的样子,平白生出许多的枝节。先生您呀,还是自己好好考虑一下吧。
民间故事:巧断风流案
民间故事:巧断风流案
山东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比岸,比较偏僻闭塞,因此豺狼当道,坏人横行。特别是有个无赖恶棍刘三,此人不夜吃喝嫖赌俱全,而且开设妓院,拐卖妇女,逼良为娼,无恶不作。
郑板桥知道范县是个污浊之地,到范县第一天,他特地喊了几个泥瓦匠来。泥瓦匠一见郑板桥就问:“何处要修?”
郑板桥说:“给我把县衙的墙壁随意砸些洞。”
瓦匠惊问房屋是否要拆,郑板桥摇摇头。瓦匠奇道:“那么为何把好端端的厚墙开洞呢?”
郑板桥说:“县衙与外面隔着墙,新鲜的进不来,龌龊的出不去。”
瓦匠又问:“以前多少任县太爷都不嫌龌龊,唯独你嫌呢?”
郑板桥哈哈大笑说:“前任偏爱空气污浊,房间发霉,我却生性爱清洁,懂吗?”
瓦匠恍然大悟,以后逢人就说:“人家说新县太爷是狂士,我看一定是个清官。”
此言传出不要紧,那些负屈含冤的百姓,纷纷投状,专告当地的坏人,特别是刘三,都告他作恶多端,一定要绳之以法。但是郑板桥想对付这样的无赖,操之过急不行,必须等待时机,揪住他,就叫他低头认罪,无法还手。
刘三听说县太爷不好对付,不由头皮发麻。按过去的惯例,知县到任必须常与地方豪绅交往,登门去拜访。
刘三虽不是富豪,但官府不但不敢惹他,反而去拜访他。奇怪的是郑板桥来到后,不但不去拜权贵,不设宴招待,反而出了个大布告:严禁买卖妇女,开设赌场、妓院,已开的要立即折除,停业。百姓无事,可以到书场听书,戏场看戏,并鼓励艺人演戏,说书。
这无形中断了刘三的财路,等于要了刘三的命。这个恶棍气呀,气得了不得,但是他是个大草包,平常吆喝可以,真正遇到这件事情,象个没头苍蝇乱撞。
这天他实在闷得慌,就进了大悲庵。刚进门,只见尼姑妙常正端着一碗茶。这妙常长得水灵灵的,刘三看见了馋诞欲滴,骨头都酥了,就挑逗说:“最近我得了一尊玉佛,改天送给你。”说着上前要摸尼姑的嘴巴。
妙常正言厉色地说:“清天白日,放尊重些。”
“哎呀,什么尊重不尊重,崇仁寺的法静摸得,我摸不摸得?”
“哼,狗嘴里难吐象牙,象你偷鸡摸狗的,再罗嗦,我就喊了。”
正在这时,只听见几声咳嗽,刘三连忙收住手,妙常乘机跑了。
刘三回头一看,原来是老尼姑。这个老尼,别看她整天抓着一串念球,其实比蛇蝎还毒,她是刘三的姘头,两个狼狈为奸。刘三见了老尼,嬉皮笑脸,老尼理也不理,一转耳进了禅房。
刘三跟着进来,一进门抱着老尼“亲娘,乖乖”地乱叫,满是胡茬的脸就要亲老尼。老尼“啪”的一个巴掌,刘三被打得晕头转向,松开老尼问:“几天不见,难到又有新欢不成?”
“啪!”又是一记耳光。
刘三改换脸面说:“打是疼,骂是爱,这巴掌打得亲切,你再打。”说着把嘴巴凑上去。
老尼拗了他一下嘴巴说:“冤家,下次再敢吃着锅里望着碗里,看老娘饶你!”
刘三直迭声地喊着,“逗你玩的,熟港熟路的,谁喜欢那个丫头片子。”说着紧紧的抱住老尼。
老尼附着他耳朵说:“你这没头脑的,有人把你给告了,新的县大爷不好惹,你给我当心些。”
“可不是,我正为这事犯愁呢,你说,不准开赌场、妓院,这不是断了我的财路吗?”
“你呀!”老尼用手指戳了他脑袋一下:“你就不能出难题难难他?”
“什么难题?”他眼晴亮了。
“哼,教会你,倒丢了老娘,不教你,让你给姓郑的抓去蹲监。”
“你真舍得?”他摸着老尼的光头皮说,“热被窝谁给你焐?”
老尼笑了,把他楼到怀中,告诉他一个主意,刘三连连称好。
再说,范县的梨园子弟,得知郑板桥提倡戏剧、曲艺,以正乡风的主张后,心中好不高兴。而且他们还看见郑板桥让人在城隍庙建成了“演剧楼”。
本来范县“秧歌剧”“花鼓戏”就很盛,只因好看一点的旦角常常被刘三无赖拐卖走。戏班子如果不常送礼,刘三就去捣乱,致使郑板桥来时,戏班子已经奄奄一息。
郑板桥一提倡,原来唱戏的当然重操旧业,会唱戏的也登台表演。那些喜欢赌的,喜欢逛妓院的看了一些新戏,受到启发,纷纷弃旧图新,安居乐业。郑板桥还制地为演剧写了一副楹联:
演古劝今,快日怡心振风俗,
穿锦唱曲,歌儿舞女闲消愁。
艺人们知道郑板桥是个戏迷,为了感激他的恩德,特地选了上好的角色,到郑府中来,要为他演一台戏,无论郑板桥如何推辞也不行。
正要开演,猛听得有人击鼓告状,好令人扫兴。郑板桥正想更衣出去,皂隶王升来了,悄悄一说,郑板桥“呵呵”大笑说“好!助兴,我正要找他们,不想他们自己送上门。”又低声问王升说:“两个被拐卖的姑娘可曾回家?”
“听说前日以动身,最迟今日再有一两个时辰可以到衙。”
郑板桥听罢,点点头,吩附王升,全班执事,一应刑具,全部准备好,还叫他们到门外如此这般做。王升会意,领命而去。
郑板桥又对优伶拱拱手说:“承各位盛悄,不过今日这戏得由我导演,让我来演出好戏给你们看。”
优伶一听郑板桥要借戏断案,而且要惩罚刘三、老尼,好不高兴。只听见郑板桥喊了一声,“伙计们,敲起来,吹起来,拉起来!”
立时一个个抖擞精神,胡琴拉得抑扬顿挫,板桥鼓敲得点到人心,笛子吹得恰到好处。万事俱备,就等开始。
你知告状的是谁?状告何人?原来原告是刘三和老尼,状告妙常与法净私通。
刘三,老尼这对姘头要为难郑板桥,就在妙常和法净身上打主意。
他们这一对年青僧尼自幼青梅竹马,情好日蜜,就设计逼迫二人卖身回家,活活拆散这对好姻缘。
两人和刘三、老尼有深仇大恨。刘三和老尼为了拔掉两根眼中钉,暗中商量,把妙常卖入娼门,再把法净卖入军伍。
无奈郑板桥上任,打破了他们的美梦,他们怎么能不恨?暗中窥视了好几天,今天终于看见了法净来找妙常。他们一看见法净和妙常在一起,立即喊一声“捉奸”。不由分说,上来就捆。
一见门口围了许多人,老尼更加得势,大吵大嚷:“想我佛门净地,你居然私通和尚,坏我庵的清名。”
妙常起先感觉到很难看,如今老尼血口喷人,就横下一条心说:“你不要假正经,你的事,别人早就给你敲过锣。”
话中有话,周围百姓哈哈大笑。原来刘三和另外一个流氓都和老尼私通,两个流氓争风吃醋,那家伙斗不过刘三,一次乘刘三和老尼私通时,他找了一面锣,一边敲一边大喊:“大悲庵着火了,大悲庵着火了。”百姓得知,纷纷提着水桶夹救火。
谁知,火没救着,倒看见老尼一丝不挂地躺在刘三怀里。所以今天妙常一说,百姓都笑得前仰后翻,有的还当着老尼的面说:“别说徒弟了,看看裤子穿没穿着。”
老尼气急败坏的说:“哼,把他们两个送郑板桥那里去,看他如何发落。”
刘三也帮腔道:“姓郑的,我看你今天怎么正乡风。”
刘三、老尼抓着妙常,法净来到衙门,这时王升出来说:“我家老爷正在后院看戏,叫你们跟我到后院去。”
一到后院,刘三抢前一步,朝郑板桥面前一脆说:“老爷子正风俗,百姓个个叫好,今天特地抓来了通奸的僧尼,请大人发落。”
妙常喊到:“大人明察,这是刘三、老尼设计陷害。”
“抓贼拿赃,捉奸拿双,你嘴还硬,老爷先打二十下。”刘三最恨妙常,自己挑逗几次,都没得手,嘴边的肉,闻得到腥,吃不到口。
郑板桥理也不理,连喊,“好,好,够味!”原来他似乎没听到他们的话,连连为戏拍的叫绝呢!
“大人,我要告状!”刘三喊道。
“什么?有戏没有板凳靠?王升看凳。”郑板桥说。
“大人冤枉!”妙常喊。
“谁说没有文场?胡琴脆,锁呐响,顿挫抑扬。“郑板桥还是不理。
王升给僧尼松了绑,给他们两把椅子,刘三还要说,王升把他朝下一按说:“看戏!你看看戏台上的对联‘乌纱不是游山县,携取教歌拍来’。我们大人是戏迷,情愿掷掉乌纱,终生与戏曲相伴,惹翻了他,拖出去打。”
刘三、老尼、妙常、法净只好不开口,看戏。
你知道的是什么戏?《风流天子》,讲的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纳马娘娘的故事。
当朱元璋唱道:“想当年,钟离乡,于觉寺,孤苦零仃无人怜,游方僧,耻气食,四方转,茹苦含辛遭犬炊。幸喜通,郭子兴,义旗高举,收元弹,许义女,花烛洞房。”
正唱到此,郑板桥对身旁的法净说:“你何不象他,也来个花烛洞房夜?”把个法净说得低下头,妙常羞红脸。
刘三一看不对,就悄悄对老尼说:“姓郑的专会捉弄人,你看看上面的戏,别又被他捉弄呀。”
老尼点点头说:“对,赶快。”
正值此时,台上鼓乐声起,朱元璋和马娘拜天地,进入洞房,一折煞尾。见郑板桥还在摇头晃脑,嘴中念着:“得锵,得锵,得得锵。”
刘三赶快跪下说:“老爷,给我们做主。”
郑板桥似乎才醒过来一般说:“好,好,到前堂,把案子断了,好再看戏。”
“升堂!”只听三通鼓响,郑板桥着官服正堂坐定,两边衙役执事站定。
刘三迫不及待地说:“大人,妙常和法净本是出家之人,却在一起通奸,被我当众抓获,望大人明断。”跟着又补了一句:“大人说,整风俗,正乡风,小人是完全拥护,望大人纯洁佛门,以正乡风。”
妙常喊道:“大人,冤枉!想我父母早亡,与姐姐相依为命,可恨刘三,拐卖我姐姐,又把我卖入庵中;屡次调戏,小尼不从,刘三从而怀恨心,诬陷小尼。”
法净也喊道:“大人,想我父母下世也早,我与妹妹相依为命,刘三把我妹妹拐走,又把我卖入寺中为奴,还想把我买入军伍。小人与妙常从小青梅竹马,同病相怜,至于通奸一事,确实没有,还望大人惩处恶人,扶救良善。”
郑板桥故意:“本官办案只重事实,从不妄听口供,你们状告刘三,无凭无据,不予受理!”
刘三一听,喜出望外,连喊:“夫人清如水,明如镜。”
郑板桥问:“妙常,法净,快把两人通奸之事从实招来。”
刘三得意地说:“快讲!”
妙常满心委屈,就学着郑板桥的口吻说:“本官断案只重事实,从不妄听口供,你说我们通奸,‘事’在哪里,‘实’在何处?
郑板桥转对刘三说:“对呀,刘三,你把事实拿出来,看他们还有何话说。”
刘三说:“今日早晨,我看见法净好象去大悲庵,就跟在后面,只见他找到妙常,两人正在一起…”
“作甚?”郑板桥问。
“谈…谈话……”
“谈话?噢!”郑板桥点点头,“有谁做证?”
“我”,老尼答道:“刘三告诉我,法净,妙常又在一起。”
“是呀,你们也谈话了。”
“是呀,她告诉我,我就说,快去,把他们抓到官府。”
“好。”郑板桥惊常木一拍,“刘三,你说,你怎么与老尼通奸的?”
“啊?冤枉!”刘三,老尼叩头如捣蒜。“怎么冤枉,他们在一起谈话是通奸,你们在一起合谋,而且平常也常在一起,岂不也是通奸吗?”郑板桥故意把平常’二字拉长,话中有话。
“哎呀,大人,小的只是谈谈而已,没有干什么勾当。”
“那么他们也是谈谈话而已,没有感这事了?”
刘三、老尼这才知道上了圈套,只好点点头说:“小的们误看了。”法净、妙常这才会心地笑了。
“好,既如此,我也不治你们的诬告罪。法净、妙常,他们都因家庭不幸被迫遁入空门,本非所愿,而且年纪又轻,同病相怜,互生爱慕之心,早盼还俗成家,本知县如让你们还俗成婚,你们可愿意?”
法净,妙常不再不好意思,一叠声地说:“愿意,愿意。”
这时刘三和老尼一起喊道:“大人,僧尼配偶不行呀。”
“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自古无例,有伤风俗,违背天理。”
这时听得后听鼓乐声起,王升出来,打了一拱说:“《武媚恨》已开演。”
“演到何处?”
“演到唐高宗到了感业寺,与尼姑武则天定为百年之好,接到工中封为昭仪。”
“混帐,为尼的怎可为帝后。”
“当时也有人反对,不过他在位多年,功绩显赫,史家都盛赞。”
“噢,唐高宗刚接位,就从庵中将为尼的武则天接出,立为皇后,传为佳话;朱元璋这个和尚,郭子兴居然把义女许配他为妻。皇帝能做,史家盛赞,可见僧尼结偶不仅合于人情,而且合乎天理。”
“大人!”老尼喊道:“那是戏文,不能当真。”
郑板桥顺手把书架上的《明史》、《唐书》朝他们面前一抛说:“史家所记,滴水不漏,怎为妄言?戏文也是以史实为据,教化愚顽,荡涤风俗。本官苦口婆心,引经据典,你们无理纠缠,是何道理?”
刘三、老尼还要无理纠缠,只听得门外一声“冤枉”,接着又是一“冤枉”两个年青女子一前一后,头顶状纸直奔大堂。
刘三、老尼一看,吓得跌倒在地,两人使了一下眼色笑说:“我们服了,大人有事,我们走了。”
“慢!今日我要当众审案。让门外百姓一齐进来,你们也帮我听听。”两人一听,吓得面如死灰。
门口早就聚集了许多百姓,一听招呼,纷纷来到堂下。
原来这两个姑娘一个是妙常的姐姐,一个是法净的妹妹,两人被刘三、老尼拐卖后,是郑板桥把她们从人贩子手中找回来的。姐妹重逢,兄妹相聚,妙常和姐姐,法净和妹妹抱头痛哭。百姓一个个都争着诉说刘三、老尼的罪恶。
郑板桥威严地说:“本官办案,只重事实,从不妄听口供,刘三、老尼逼良为娼,拐卖妇女,败坏风俗,无恶不作。来人,先打刘三、老尼各二百板,重枷关进大牢。”众人无不称决。
刘三、老尼被押走了,这时优伶们一起走到前堂说:“大人,今天你演的戏真是唱念做打,处处见功呀!”
“哪里,哪里,不过我要给你们写一本《僧尼缘》,谁人给我演呀?”
法净、妙常都不好意思地笑起来。郑板桥说:“你们受尽磨难,终成伉俪,我无甚相送,仅赠诗一首。”说着提起了判笔:
“一半葫芦一半瓢,
合于一处好成桃。
是谁了却风流案,
记取当年郑板桥。”
以上内容是小编整理的关于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和出道仙和出马的区别的优秀文章,喜欢小编发表的出道仙和出马仙哪个道行高和出道仙和出马的区别请一定要在下面浏览哦,我们将第一时间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