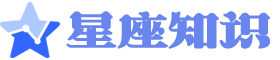西王母,山海经 《山海经》的西王母
你现在浏览的是一篇关于西王母,山海经的精彩内容,本文拥有《山海经》的西王母和西王母,山海经的精彩内容发布,喜欢的关注本站。
西王母,山海经 《山海经》的西王母
山海经的传说
读书笔记:《山海经》系列(6)刘宗迪:西王母神话地域渊源考
逸飞按:刘宗迪以《失落的天书》一书成名,是当代《山海经》研究的健将之一,然观其《西王母神话地域渊源考》一文,狂妄自大,逻辑混乱,硬伤迭出,实令人大失所望。
以下摘其一点论述,可见一斑:
周穆王西征,见西王母,这是西王母神话“西方说”的重要根据之一。《史记》载之于前,汲冢《竹书》发之于后,又有《列子》作为旁证,可谓证据确凿。《竹书纪年》、《穆天子传》或许有后人的增饰,《列子》可能是文人的想象发挥,对它们的记载尚可质疑,但是,《史记》是严肃的历史著作,太史公总不会捕风捉影吧。
但是,奇怪的是,司马迁尽管在《赵世家》中提到周穆王西征之事,在《周本纪》中叙述周穆王的事迹时对其西征却只字不提,此外,在《秦本纪》中追溯秦人祖先时也提到造父御穆王西征之事,但也决口不提见西王母事。据《穆天子传》,周穆王御驾西征,足迹所及,行程上万里,遐方诸国纷纷逢迎礼遇,其事雄哉壮矣,正应该是史家所艳称的先王盛事,周朝史官本应大书特书,但司马迁在《周本纪》中却只字不提,这实在是意味深长。(逸飞按:纪传事迹互见本为《史记》之特点,刘宗迪却拿来说是硬伤,难道太史公也必须像当代人那样啰嗦才行?)
袁珂先生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说:“前人尝讥作《史记》的司马迁‘好奇’,把一些神话传说的材料采入书中,但史公对《穆传》、《竹纪》材料的使用还是谨慎的,在《周本纪》的穆王传中就没有提到穆王见西王母事,只是在《赵世家》里才从侧面简略地提到,把此事当做一段赵族先祖发迹的传说来稍事点染罢了。这种处理从史学的角度说来还是比较恰当的。”但袁珂先生没有解释太史公这样处理的缘故。(逸飞按:《穆传》、《竹纪》皆迟至西晋初年才出土,难道西汉的司马迁可以穿越到西晋?司马迁压根就没见过的史料,你让他怎么引用?)
这一点其实并不难解释,其在《赵世家》中提到这一故事,旨在借以说明赵氏的来历。一个姓氏或民族的来历,原本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它和一切溯源性解释一样,都是后人依傍之辞,皆非有史实可资凭据者。《史记》所载许多民族和家族起源的故事,绝大多数是荒唐谬悠、无可稽考的神话,甚至连太史公自述家世也不例外。司马迁引用造父御周穆王西征之故事说明赵姓来历,正如他在《殷本纪》中引用女狄食鸟卵而生商人的祖先契以说明商人的来历,在《周本纪》中引用姜嫄因踩到巨人的足迹而生周祖弃以说明周人的来历,在《秦本纪》中引用秦祖孟戏、仲衍鸟身人言之说以说明嬴姓的来历,只是引用民间传说姑妄言之,并不意味着太史公相信实有其事。(逸飞按:此论严重侮辱司马迁的智商,好像司马迁压根就分不清民族感生神话和历史传说的区别。你以为你是谁?)
但《周本纪》在叙述穆王事迹时,因为穆王时周人早已建国,王者之起居出征必有史官付诸笔札,故叙述穆王的事迹就只能依靠传世的史料,就不能不慎重区分真的史实和假的故事,只有确凿有据的才能载入史册,因此,在《周本纪》穆王纪中,司马迁只叙述了穆王征讨犬戎和作刑书的故事,因为两者都是“有典有册”可以稽案的,前者见于《国语》,后者见于《尚书》。(逸飞按:此论严重侮辱司马迁的史德,好像司马迁明知故事有假也要装糊涂将之载入史册。
《山海经》系列(6)西王母神话地域渊源考
《山海经》系列(7)从出土简帛破解《山海经》身世之谜
山海经的传说
读书笔记:《山海经》系列(7)陈民镇:从出土简帛破解《山海经》身世之谜
在陈民镇看来,考古发现或许是破解《山海经》身世之谜的一种方式:浙江良渚的人面兽身神徽、安阳殷墟的虎首人身神兽、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雕像、山西九原岗的北朝壁画、商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都能窥见《山海经》的踪迹。
1942年,盗墓贼在湖南长沙城东南郊的子弹库战国楚墓发现了一件帛书,记录了伏羲、共工等创造并维持宇宙的神话,这便是著名的子弹库帛书,又称楚帛书。楚帛书上绘有12个人兽杂糅的神怪,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指出它们是十二月神,现在已成定论。
陈民镇介绍,这些月神的形象,酷似《山海经》对一些神灵的描述。比如,春正月的神是“蛇首鸟身”,春二月的神是“四首双身连体鸟”,夏四月的神是“双尾蛇”,夏五月的神是“鸟足三头人”,等等。其中,夏五月神的形象,还可与《山海经·中山经》“其神状皆人面而三首”的记载相对照;《山海经·海外南经》中也有“三首国”的描述。
陈民镇说:“楚帛书中的神与《山海经》中的神并不是一回事,夏五月神的形象与《山海经》相吻合也只是偶然,但两者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反映了当时人们心中神祗的形象。”
除了帛书和帛画,从战国秦汉的简牍中也可以发现《山海经》的线索。比如,简牍《日书》(类似“黄历”,古人用来选择时日、推断吉凶,从楚简到秦简、汉简,版本众多)中就有许多内容与《山海经》有相通之处。《日书》中的“穷奇”是一种吃梦的神兽,通过向它祈祷,可以驱逐梦魇,而“穷奇”在《山海经》中也有类似描述。《日书》中还有“是状神在其室,掘□泉,有赤豕,马尾,犬首,烹而食之,美气”的记录,这一“马尾、犬首”的“赤豕”,便颇似《山海经》中的怪兽。
在先秦文献中,大量记录神话的著作,除了《山海经》,还有《归藏》。《归藏》相传是商人的易经,已经亡佚,后人根据残存的只言片语作了大量辑佚工作。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发现,为今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在秦简《归藏》中,涉及女娲、黄帝、炎帝、蚩尤、夏启、禺强、赤乌、黄乌等神话形象,可以与《山海经》对读。
《山海经》系列(7)从出土简帛破解《山海经》身世之谜
《山海经》系列(8)《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
山海经的传说
读书笔记:《山海经》系列(8)武廷海:《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
(城市设计,2023年1期)
《汉书·艺文志》共收书596家,计13269卷。在“术数”这个大类中,又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6个“小类”。《汉书·艺文志》收录“形法六家,百二十二卷”,依次为:
《山海经》十三篇;《国朝》七卷;《宫宅地形》二十卷;《相人》二十四卷;《相宝剑刀》二十卷;《相六畜》三十八卷。
可惜,这六部形法书籍如今除了《山海经》尚存传本外,其余悉已亡佚。……十分难得的是,《汉书·艺文志》有“小序”阐释“形法”知识的旨趣:
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徵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然形与气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无其气,有其气而无其形,此精微之独异也。
根据形法序文所述,《汉书·艺文志》所收录的六部形法书籍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相地,包括《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三部书,相当于形法小序中所说的“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一类是相人相物,包括《相人》《相宝剑刀》《相六畜》三部书,相当于形法小序中所说的“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在古人看来,世间万物,莫不有形。天有天象,地有地形,人有面相、手相、骨相、体相,六畜、刀剑亦各有其相。“形法”的要义就在于“相术”,即通过对世间万物有形之体的观察而求声气贵贱、吉凶。
相地和相人相物这两类书籍都被《汉书·艺文志》归为“形法”,说明两者在相术原则上具有共通性,在相术方法上具有一致性。元代吴澄(1249-1333年)即认为“相地”与“相人”属于同一种“术”,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于其形而观其法”:
或问:“相地、相人一术乎?”曰:“一术也。”吾何以知之?从《艺文志》有《宫宅地形》书二十卷、《相人》书二十四卷,并属形法家,其叙略曰“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又曰“形人骨法之度数,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然则二术实同出一原也。后之人不能兼该,遂各专其一,而析为二术尔。庐陵郭荣寿善风鉴,又喜谈地理,庶乎二术而一之者。夫二术俱谓之“形法”,何哉?盖地有形,人亦有形,是欲各于其形而观其法焉。虽然,有形之形,有不形之形,地与人皆然也。形之形可以目察,不形之形非目所能察矣。余闻诸异人云。(元·吴澄.赠郭荣寿序//李修生.全元文.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97)
鉴于相地与相人相物术的共通性与一致性,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相人相物术中“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的含义,来把握相地术中“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的基本精神。……形法是一种关乎“数”的“术”,这是从相人相物术而得出的基本判断,对于我们一般认识“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的相地术,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形法”通过观察事物的“度数”“形容”等物质特性,推测现象背后隐藏的东西,而占其贵贱、吉凶,在古时看来,这是一套具有实用功效的专门技术,与人们的生产实践息息相关。
从《山海经》入手,可以一窥相地类形法书籍的基本特征。
东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约公元30-85年)因治水功业有成,永平十二年(69年)得到皇帝赏赐的《山海经》。《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传》记载:
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问以理水形便。景陈其利害,应对敏给,帝善之。又以尝修浚仪,功业有成,乃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及钱帛衣物。
王景少年学《易》,广窥众书,又好天文术数之事,沉深多伎艺,以能治水而知名,皇帝赐之以《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可见《山海经》应当与《河渠书》《禹贡图》类似,即在地理尺度上涉及全国或九州的范围,在内容上与人们的实际生产与生活利害攸关,王景在治水中通过“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等措施,可能与《山海经》不无关系。
今人根据传本《山海经》的研究中,唐晓峰认为《山海经》所载地理知识具有两重性,分别源自天神信仰和现实经验(唐晓峰.从混沌到秩序:中国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论.北京:中华书局,2023),苏晓威认为《山海经》呈现的是一定人群对山川自然形势的经验性地理知识(苏晓威.出土文献《地典》《盖庐》的研究.九州(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可以说,《山海经》所载的是古人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属于“基本国情”,文字描述比较平实具体,对于立国建都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地理根据。
《山海经》系列(8)《汉书·艺文志》中的“形法”
以上内容是小编整理的关于西王母,山海经和《山海经》的西王母的优秀文章,喜欢小编发表的西王母,山海经和《山海经》的西王母请一定要在下面浏览哦,我们将第一时间给你回复!